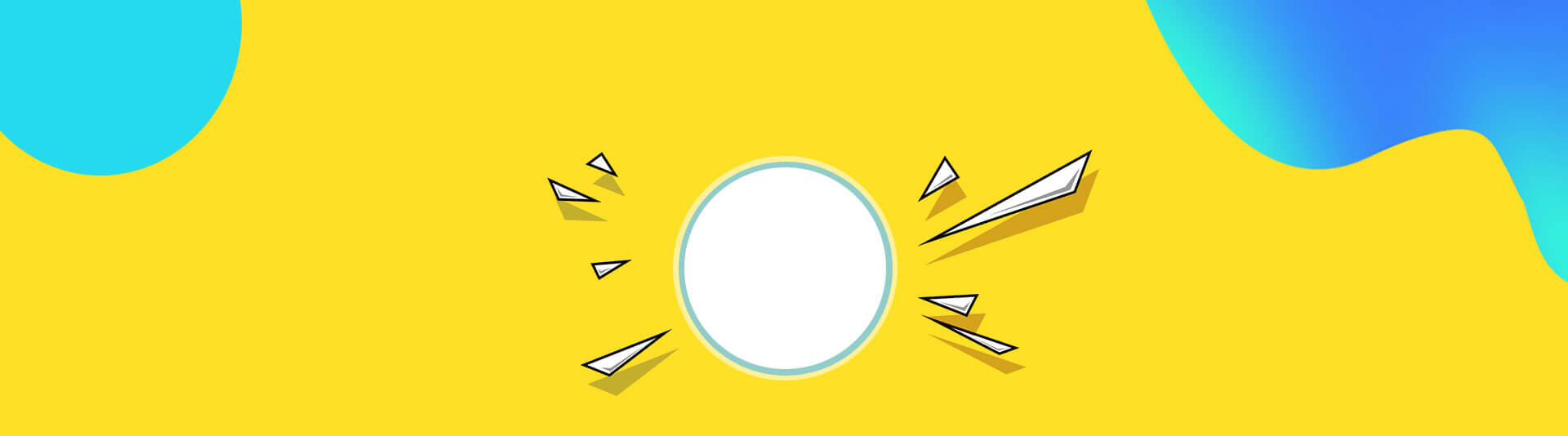1952年8月1日清晨,天安门广场上第一声汽笛响起,吊车的钢缆缓缓绷直,数十名工人同时发力,巨大的灰白色花岗岩被稳稳送上月台。有人小声提醒:“今天是动工第一天,千万别出差错。”就在这一刻,三年前的一个场景又浮现在不少人的脑海——那年9月30日,毛主席在同一片土地上铲下第一锹土,一个国家给英雄们的承诺由此写下序言。

奠基典礼其实筹谋已久。1949年初,北京尚未完全从战火中复苏,几位北平市政人员就在讨论:首都总要有一座能让后人抬头便想起牺牲者的纪念物。议案被送到中央,很快得到肯定,只是究竟该放在什么地方,一时众说纷纭。
先有人建议东单,说那边车马人流大,看的人多;也有人看好八宝山,那里埋着革命先烈,气氛庄重。然而周恩来把图纸铺在桌面上,指了指正中的一根红线:“天安门广场,中轴线上。”短短一句,后来的诸多争执瞬间有了方向。
选址还没最终拍板时,周总理亲自爬上天安门城楼。风很大,他眯着眼环顾四周,旁边工作人员问:“总理,这么看有什么结论?”周恩来摇头:“得再走一圈,脚下量出来的距离比眼睛准。”一个上午,他在广场上足足来回测量七次,傍晚才说出那句耳熟能详的话——“位置定下了吗?”
9月30日下午,政协代表刚散会,周恩来又到主席席前低声商量:“趁夜色未深,把奠基典礼办了。”毛主席点头。于是夜幕下车灯一排排射亮广场,朱德、刘少奇、宋庆龄等人依次而立,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奏起,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。毛主席挥锹破土时,尘土飞扬,他停了一秒,把锹头压得更深,像是在给这片土地落上一枚钢印。
值得一提的是,当晚奠基石比后来实际位置偏北几米,更靠近天安门城楼。设计师梁思成第二年复核尺寸时发现:广场纵深略显局促,再往南挪更协调。于是他托人请示彭真,彭真摆手:“主席忙,方案你们定,量准就行。”就这样,奠基石后来又悄悄向南移动,才有了如今的广阔视野。

纪念碑叫什么、写什么,同样没少费心思。毛主席写下八个大字“人民英雄永垂不朽”,先后誊写两稿,每个字不到一寸见方。1205工厂的技术员拿到稿子先放大,再去毛刺,保证边锋不走样。刘开渠把放大样描了一遍,还嘱咐石工:“哪怕磨掉十把钻头,也不能失了那股气劲。”
碑文由谁执笔,彭真提名周恩来。总理白天批文件,晚上练字,一连写了四十多遍,挑出最满意的一幅递给刘开渠。“字行不行?”周恩来问。刘开渠把稿纸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,只说一句:“够分量,刻上去就是定海神针。”短短150字,之后被制成“阴文圆底”,每一笔都嵌进花岗岩里,深度恰好一公分,既能排水又不易积尘。
1951年国庆,三座不同风格的模型被摆在广场中央,任群众打分。有人偏爱雕像式,有人喜欢碑墙式,但多数人指着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方案说“看着顺眼”。票数统计完毕,方案基本确定:碑体37.94米高,坐南朝北,底座九层。坐向的改变源于周恩来一次登楼,他指着正北说:“长安街来往车辆多,第一眼就要看到毛主席题词。”

正式动工那天,梁思成身体欠佳,仍撑着病体来到工地。他盯着吊车缓缓放下的第一块根基石,轻声嘀咕:“花岗岩没选错,五百年也不怕风化。”旁边年轻技师听不懂,又问:“梁先生,为何把碑身三分之一处收腰?”梁思成抬手比了个弧线:“中国传统屋檐讲‘飞’,西方古典柱式强调‘挺’,收腰就是在‘飞’与‘挺’之间找平衡。”
1953年10月13日,装载碑心石的专列进了前门西站,朱德赶来迎接。他拍着负责押运的老工人肩膀:“这一块石头,是几万条命托着的。”从车站到广场不过两公里,钢管滚轮一路接力,用了足足十二个小时。次年3月7日正式吊装,工地一片寂静,哨声一响,几百双眼睛盯着空中那块重达六十余吨的白石,直到稳稳卡进石槽,一声锣鼓打破沉默,很多人激动得说不出线日,全项目验收完毕。工人撤离前,最后一道工序是给碑文描金。魏长青脱下鞋,赤脚踩在脚手架上,一笔一笔刷,无声却凝重。5月1日揭幕,几乎全城人潮涌向广场,花束铺满台阶。从那天起,这座碑成为首都几何中心的坐标,也成为无数家庭讲述往昔的引子。
有人统计过:从提议、选址、设计到完工,纪念碑共用时九年,参与人员超过万人次,方案修改二百余次。更难得的是,无论争论多激烈,“人民英雄”这四个字始终没被触碰。它们像钉子一样钉在所有人的心里,提醒设计者、工人、乃至后来每一个路过的人——纪念碑的真正主人在地下,在历史深处。

1961年,纪念碑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之后的岁月里,碑体经历保养、描金、加固,外观几无变化,但材质和工艺却一次次升级。有人说,这叫“修旧如旧”。技术员更多时候只用一句话来解释:“英雄不能褪色,碑也不能。”
今天走进广场,北看五星红旗,南望毛主席纪念堂,东是国家博物馆,西为人民大会堂,正中央这座花岗岩长碑像是一位沉默的哨兵。它不言语,却时时提醒:名字被镌刻的不只有过去,还有一种永不退让的精神。